1900年秋天,年仅19岁早熟的毕加索还不为人所知。这一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和他的朋友,西班牙诗人、画家卡洛斯·卡萨吉玛斯(Carlos Casagemas)从巴塞罗那乘火车来到巴黎,目的是看自己的作品挂在世博会西班牙馆。这件作品是1898年创作的《最后时刻》(Last Moments),1903年将其覆盖重新绘制为《生活》(La Vie),这是他“蓝色时期”的巅峰之作。
5月12日,“年轻的毕加索在巴黎”(Young Picasso in Paris)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开幕,该展是“毕加索庆典1973-2023”的一部分,虽然仅展出了10幅作品,却探索了毕加索在关键的一年创作的演变,展示了“成为毕加索之前的毕加索”。
1904年,毕加索在巴黎蒙马特“洗濯船画室”。
 (资料图)
(资料图)
展览由古根海姆现代艺术策展人梅根·丰塔内拉 (Megan Fontanella) 策划,是欧美博物馆“毕加索去世50年”举办的30余场展览之一。这些展览反映了在艺术家去世半个世纪后,继续影响着新的一代,而且仍然蕴藏着有待学者和新技术发现的奥秘。
古根海姆博物馆以“毕加索庆典”为动力的研究于2018年启动,馆藏毕加索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巴黎煎饼磨坊》在修复和研究后,成为展览的核心。这幅作品描绘了一个舞厅,里面坐满了穿着优雅、漂亮的男人女人,他们跳舞、喝酒、谈笑风生;也有人目光游离,似乎在随时寻找下一个话题。它相对安静,一个完全了解其时尚、肢体语言和人际关系的艺术家画下了温文尔雅、世故的人群。
毕加索到巴黎,更大的使命是希望树立自己的声誉,他参加了现代法国绘画的速成班。在此期间,他与其他艺术家共用工作室和模特,贪婪地体验着这座城市提供给他的一切。他是一位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善于交际的外来年轻艺术家。他去博物馆看经典艺术品、去美术馆看最新艺术潮流。他在咖啡馆、卡巴莱(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和舞厅享受迷人的波西米亚夜生活,“煎饼磨坊”(Le Moulin de la Galette)是其中最著名的。
他开始在巴黎社交,最初是西班牙艺术家和作家,其中一些是巴塞罗那的旧识,随着法语的学习,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巴黎人。
他思考借鉴着前辈艺术家的绘画风格——雷诺阿、图卢兹,尤其是瑞士出生的插画家泰奥菲勒·斯坦伦(Théophile Steinlen),可能还有点修拉。所以舞厅的顾客带着流畅、平静的古典形式。
在普遍的黑暗中,男性的黑色外套与女性颜色微妙、面料多样的服饰交替出现,巴黎社会的横截面在电灯下交汇。他对明亮空间的华丽渲染,虽充满活力,却也令人不安。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毕加索对委拉斯开兹和戈雅的热爱,也可能与拉蒙·卡萨斯(Ramon Casas)忧郁而柔和的空间描绘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幽暗的展厅,凸显出各种画中的颜色——在《侧面的女人》(Woman in Profile)和《戴帽子的妓女》(Courtesan With Hat)粗糙的点彩、《食客》(The Diners)的红色地毯……在唯一一瞥日光的《1901年7月14日的游行》中——来来去去红、白、蓝的笔触暗示着一种印象派的激荡。其中,《巴黎煎饼磨坊》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却不容低估。这是毕加索在巴黎完成的第一批画作之一——记录了在巴黎最初两个月,艺术家的创作被沉浸式的改造。这也是第一件进入法国收藏的毕加索作品,它最初通过艺术品经销商贝尔特·威尔(Berthe Weill)卖给了出版商和收藏家亚瑟·哈克(Arthur Huc),后者在发现毕加索方面的作用常常被忽视。
《巴黎煎饼磨坊》自2021年11月起不再展出,博物馆的高级绘画保管员朱莉·巴滕(Julie Barten)负责对它进行了的清洁和修复。她一丝不苟地清洁表面,用棉絮和湿纸擦掉一层污垢和几十年前覆盖其上的发黄的清漆。修复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在高科技仪器辅助和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研究人员的援助下,煤气灯的光芒更加明亮;空间更具景深、高礼帽、酒瓶和玻璃杯更有立体感,同时也揭示了毕加索在创作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变化——画面左下角的黑色上,曾有一只赤褐色皮毛、系着朱红色的蝴蝶结的查理王猎犬在上面休息;桌边还放着一把空椅子。
这场展览中另一个最精彩的时刻是一幅1900年用炭笔和蜡笔绘制的充满活力的画作,它来自欧洲的一个私人收藏,这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如同一张“自拍照”,描绘了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世博会。这些朋友就包括了毕加索和他的女友奥德特,以及卡萨吉玛斯和杰曼·加加洛(奥德特的妹妹)等,也正是杰曼导致了卡萨吉玛斯的自杀。在画中,毕加索以来自不同方向黑色笔触的重叠表现出他们挽着胳臂,身体倾斜的嬉闹气氛。毕加索绘画天赋在画中人的动态上显而易见,这一次前景中的查理王猎犬没有被抹去。
展览偏重毕加索对巴黎社会生活的描绘,但巴黎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接受毕加索。在这里他是一名嫌疑人、一名外国人,被警方跟踪,被贴上“威胁社会安全”的标签。警方的档案里,塞满了他的报告、审讯笔录、居住证、身份证照片、指纹、租金收据和入籍申请。 甚至,法国主要的国家博物馆一度拒绝展出或收藏他的作品。比如1929年,卢浮宫拒绝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作为礼物入藏。即便在当时这幅画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杰作。直到“二战”后,法国才对毕加索发生了改观,当时毕加索已经是一个票房宠儿,他开始向法国省级博物馆捐赠作品。他知道慷慨会给他带来什么,这是在公共领域播种种子,让更多公众看到和了解他的作品,传播他的品牌。这都是后话。
1935年,毕加索在巴黎申请外国人身份证的档案。
展览两件极具个人风格的自画像,记录了初到巴黎的毕加索。
毕加索去巴黎前的几个月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度过。其中一幅自画像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显示了一位艺术家以准表现主义笔触的黑暗背景下,强调着自己强烈而灼热的凝视,他脸的周围环绕着蓝色的光环。
另一幅更著名的自画像创作于1901年的最后几个月,他于这年5月中旬重返巴黎,准备在画商伏勒尔(Ambroise Vollard)的画廊举办他在巴黎的首次个展。 这个四分之三侧面展示了艺术家强大的个性,扁平的蓝色背景趋向于展厅墙壁的颜色;他苍白冷酷又犹豫不决的表情和厚实的黑色大衣,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即将随船沉没的船长。
这两幅画打开了通往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大门,摆脱了他在巴黎第一批画作中更明亮的色彩和情绪,引入了一种更原始的模式(尽管受惠于格列柯和象征主义)转向内心、走向毕加索内在气质的忧郁,他持续的贫困和他对朋友卡萨吉马斯死亡的哀悼。1901年2月,卡萨吉马斯在巴黎,当时毕加索在西班牙。 这幅令人难以忘怀的自画像为毕加索对“光明之城”的热情洋溢的欣赏画上了句号。
“年轻的毕加索在巴黎”不仅是了解这位艺术家早年岁月的窗口,还展示了正在转型的艺术家。巴黎显然给毕加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多样性的景观和文化能量深深吸引着年轻的艺术家,促使他自由的追求,他自己也留给世界不可磨灭的印象。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编译)(注:展览将持续至8月6日,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OBSERVER》、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官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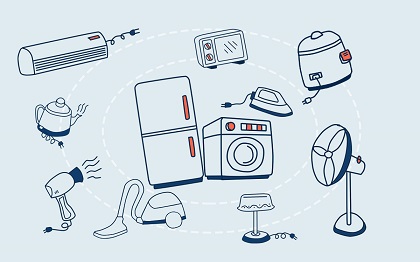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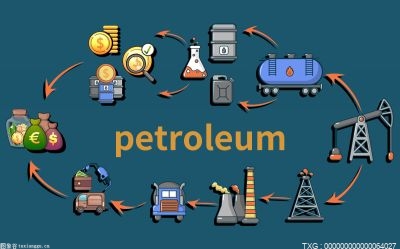















![牡丹江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IV级/一般] 【2023-05-13】](http://img.qipei.nanfei.cn/2023/0513/20230513122340834.jpg)